分享到微信朋友圈x
打开微信,点击底部的“发现”,
使用“扫一扫”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。

- 返回目录
- 上一篇
- 下一篇
- 放大+
- 缩小-
- 常规
朱阅平:向时代述说
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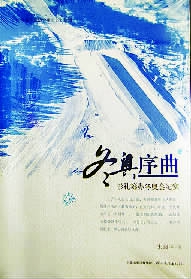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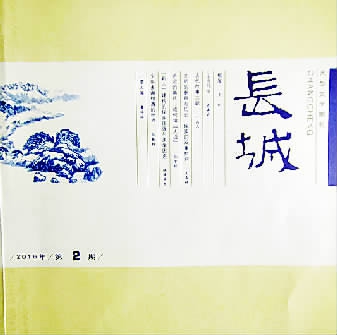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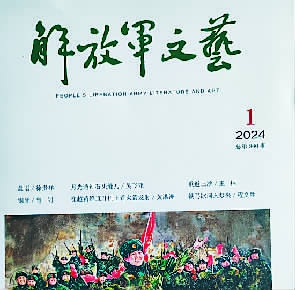 |
|
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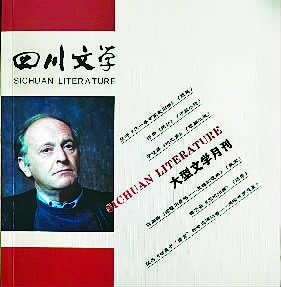 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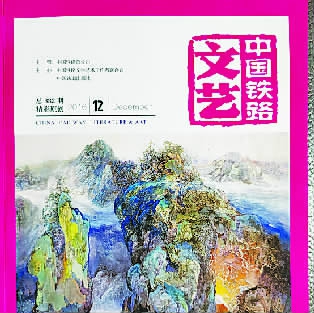 |
|
 |
作品刊登在部分杂志上 |
编者按:前不久,我市崇礼籍作家朱阅平中篇小说《护林侯》同时获得两个奖项,一个是入选河北省文学榜,一个是“兴文杯”第七届中华宝石文学奖小说提名奖。小说描写在扶贫搬迁村里,一位老人独自种粮、种树、护树几十年的故事,探讨了农民在这场变革中的主动性,对时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。
写作收入低,朱阅平不在意,“就像走路,每一步付出的代价都不大,坚持下来可以走很远,难在坚持。坚持就是忍耐,闷着去忍耐。”他说自己的生活极度简单,真正的波澜都在心中。
二十年来,朱阅平以平均每年40万字作品的速度,创作了《一枪火药》《冬奥序曲》《紫桦林》等作品,以文学的形式创造着可以“向时代述说”的价值。
本报记者 郝莹玉
第一次发现朱阅平是个有故事的人,因在几年前读了他的一首散文诗:
“那天,我走得急,未顾及送子娘娘塞给我的丑面皮。也许,那是一个忘记带伞的雨夜,注定承受人生的苦雨。”
“谁细细观察过一株小草悄悄地生长,默默地枯荒、衰亡地不声不响。有谁留意蒲公英为人准备了一生的小伞,最终自生自落,在寂寥的荒野流浪。只有孤独躲在树后热泪盈眶——”
尽管他散文诗的结尾,有一种不屈的倔强,但那种无助的绝望还是扑面而来。是怎样的经历使他发出如此沉重的低吼呢?苦难是世间的常客,但在苦难中沉沦还是在苦难中奋起,那就因人而异了。对苦难对世界有深刻的思考,更难能可贵。
朱阅平黝黑的皮肤、睿智的目光,瘦削的脸孔上被时间刻下深长的印痕。他像一口古井,总有挖掘不完的新奇抑或坚韧的力量。
借来的文学书籍
“倒扑烟的灶台,漏雨的草房,土炕躺个病老娘。”这句谚语正是朱阅平少年时的生活写照。
年少的他,经历着生活的难。但随着崇礼白旗乡上窝铺村里大喇叭,持续半年喊村医钱学朝来拿书的声音,渐渐唤起他的好奇。当他得知钱学朝在写诗,便大胆地问:“我能写吗?”钱学朝说:“行呀!”朱阅平幻想给自己插上一双翅膀,这翅膀就是文学,他斗胆自学写点东西。
20世纪80年代,钱学朝带领村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起探讨文学创作。朱阅平便是其中的成员。
学习、读书,前提是有书。朱阅平这时才发现书比钱还少,他开始四处找书,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偏远山村,带字的纸都不多。他找遍了全村几十户人家,只找到十几本“小人书”和几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。好在有三级党报,人民日报《大地》、河北日报《布谷》、张家口日报《长城》副刊登载文学作品。报纸一周来一次,朱阅平在每个来报纸的当天晚上,都会到大队部翻看报纸。上面的文学作品,成了注入他文学之肌的唯一汲养。
一次去县城为母亲买药,朱阅平意外发现大街上报刊亭里有文学刊物,卖书的是一位40多岁的大姐,她穿着邮局绿色工作制服,给人庄重的感觉。朱阅平要过一本《诗刊》,捧在手里舍不得撒手,徜徉在诗句的意境里。一个轻轻地声音问:“你买不?”他惊醒,顺口说:“买!”就从身上掏出钱,钱在手里硬邦邦地提醒他,身上带的17元钱,是给娘买药的。他举着手里的钱支吾着:“这,这是给我娘买药的钱,下次我一定买。”大姐看着他善意地笑了。
从那以后,朱阅平一有空闲就借自行车跑到县城,直奔报刊亭。然后假装买书,挑选着看一会儿。他把时间定在半小时之内,觉得30分钟,是这个善良大姐对他不买而看的承受底线。每次朱阅平把书递还给她的时候,她都意味深长地看朱阅平一眼,每一眼都在消磨朱阅平继续骗书看的决心。
就这样,朱阅平在不安中一年到县城11次,阅读了一些诗歌和精短小说。他开始忐忐忑忑地写诗了。于是,树叶、山崖都留下了他创作的诗歌……
挤出的创作时间
有一天,听人说他有一首小诗展露报端,这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。那一年,他20岁。
但他没有陶醉在眼前的成绩中,依旧独自一个人寂寞走着文学的夜路。从有梦那天起,他就梦想有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,像那些名家一样,可以拥有所需的书籍资料,可以拥有采风的时间和资金,可以拥有专心创作的心情。
然而,十几年来,背井离乡,整日为生存奔波。
那些年,打工繁重而长时间的劳作,根本没有读书时间。他每年整理起可以读书的散碎时间不足15天。
有一年,朱阅平拥有了连续20天的读书写作时间。当时他到一家集体金矿打探洞,早上5点起床,每天劳作11个小时。那时没有风钻,都是手工打炮眼,工作面要打6个一米深的炮眼,每个炮眼都是一锤一锤地砸进去,平均每10锤最多进1厘米,遇到硬石头,需要时间更多。手上是上午一茬炮,下午一茬炮。然后再把炸下来的石头用手推车推到洞外。每车有500多斤重,两个人推一车都很吃力。
半年下来,朱阅平累得病倒了。在炕上整整躺了二十天。看病把半年挣得工钱又都花掉了,只赚了一个瘦弱的身体。养病这些日子,他对人生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,趴在炕上用铅笔和砖厂糊窑麻纸一口气写出了八十多首诗。生活的压抑、艰难和生命的摧残,使他的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。八十首诗中有四首获奖,其中组诗《天下母亲》获一等奖。
从华北打到中原,从东北打到西南,打工的脚步没有停,依旧不变的是繁重的劳作和挤时间的写作……
“为了生存,我先后干过采矿工、采煤工、砖窑工、保安、建筑工、机修工等十几个工种,苦难的经历和怀揣着文学的梦想,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”朱阅平说,渐渐地他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变,从自信变得自卑,又从自卑变得自信,从把生活看作难以逾越的苦泽,变成可以汲取营养的乳河,从不满到愤恨,从愤恨到思索,从思索到平和,从平和到创作。
随着文学作品不断在报刊发表,朱阅平从工地走进了机关。
一次,加班结束已是午夜,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,在胡同里与两个人擦肩而过,听的其中一人说,又是一个喝醉的。他回家躺在床上失眠了,没想到自己会累成一个喝醉酒的状态。
为时代书写历史
如今,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朱阅平,凭借着《一枪火药》《冬奥序曲》《紫桦林》等作品让他的文学创作,逐渐有了影响力。创作体裁涉及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剧本等。
“写诗也是人的一种本能,如悲伤就哭,欢乐就笑。欲笑无声,欲哭无泪,就写诗。无病呻吟,糟踏诗。写诗不必只努力技巧,最应努力的是未有感触时努力不写诗。考虑诗的市场,就是对诗的亵渎。诗本身就很孤独。”朱阅平这样理解诗歌创作,但他担心的是,我们所写的诗,怎样唤醒更多的大爱。
他小说的目光更加深邃,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,关注时代的变革。中篇小说《护林侯》描写一个扶贫搬迁村里,一位老人独自种粮、种树、护树几十年。小说以对万亩山林的固执守护,串联起人与自然相处的宏大命题。《枪响一声》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,朱阅平调用了自己多年的文学积淀,来成就一个真实的抗战传奇。评论家冯海燕认为他的小说有风度,小说创作要专注于精神的东西,从生活体验飞跃到生命体验,把风度切入小说最好。
朱阅平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;张家口市作协副主席、民协副主席;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;崇礼区政协历史文化研究办公室主任。鲁迅文学院河北高研班结业,《长城文艺》编委。近年出版、发表大量文学及历史文化作品。
在《解放军文艺》《长城》《天津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黄河》《山花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60余篇;出版《一枪火药》等长篇小说3部;出版《冬奥序曲》等长篇报告文学4部;出版小说集《紫桦林》。
短篇小说《秧歌老太》入选河北省2015年度小说排行榜;短篇报告文学《“村民”姚俊》入选河北省2017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;《金花鼠铸魂记》入选河北省2021年度文学散文榜;《护林侯》入选河北省2023年度文学小说榜;长篇报告文学《冬奥序曲》,获河北省第十四届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
“在小说《护林侯》中,我想探讨的是,农民在这场变革中的主动性,对时代的作用到底有多大?农村是农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,城市化有没有可能带着农村一起前行?换言之,农村建设怎样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,让农村长成蕴含乡愁的另一种城镇。抑或让农村成为城市化的基石,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。”朱阅平说,他就是一个对乡土文化寂寞地守望着,努力用文学为人民和时代书写历史。
